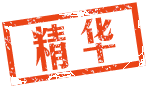本帖最后由 weiliqiang 于 2014-7-30 18:17 编辑
苏绰“六条诏书”的治国思想评析 本文摘自《管理学者》,作者刘文瑞
西魏苏绰提出的“六条诏书”,构成一个完整治国方略框架,实现了“顶层设计”和基层操作的结合,体制建构和习惯演化的结合,从而完成了由秦汉到隋唐的治理思想过渡。在管理思想上,“六条诏书”兼容儒墨道法各家学说,大处着眼,小处着手,在帝制时代的治道探究上做出了新贡献。
北朝后期,苏绰辅佐宇文泰,在西魏推行《周礼》之制,以提出“六条诏书”而闻名。他的“六条诏书”构成一个完整的治国方略框架,实现了“顶层设计”和基层操作的结合,体制建构和习惯演化的结合,从而完成了由秦汉到隋唐的治理思想过渡。“六条诏书”包括“先治心,敦教化,尽地利,擢贤良,恤狱讼,均赋役”,此六者互相关联,配合呼应,构成一个整体。在管理思想上,“六条诏书”兼容儒墨道法各种学说,贯通学术与实务,以崇尚周制并切合西魏现实作为治国总纲,把提纲挈领的宏观视野和细节操作的具体规范相结合,大处着眼,小处着手,在帝制时代的治道探究上做出了新贡献。研究苏绰的管理思想,可以在传世与实用、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得到新的启示。
苏绰的“顶层设计”
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动荡,隋朝最终重新统一了中国,而隋朝统一的根基是由西魏北周奠定的。在西魏北周的国家治理中,有一个人物功不可没,这个人就是苏绰。南宋叶适曾经说过如此话语:“自宇文泰起接隋唐,百年中精神气脉,全在苏绰一人。”(《习学记言序目》)
苏绰是武功人,字令绰,出身官宦世家。“博览群书,尤善算术。”(《周书·苏绰传》)他的一个从兄苏让出任汾州刺史,西魏的实际执政者宇文泰问其家里还有谁堪任官职,苏让就推荐了苏绰。于是,苏绰被召为行台郎中。但是,很可能宇文泰也就是说说而已,没把这位新来的郎中当回事,一年多并未重用他。苏绰似乎也没有主动向高层靠拢的迹象,而是把自己的才能用在基础工作上,把主要精力用于公文格式的设计和规范。也许是这种格式化标准化的工作过于琐细,使宇文泰觉得苏绰不过如此,所以,尽管“台中咸称其能”,但宇文泰并未放在心上。
转机来自于一次大臣奏对。宇文泰有一天同行台仆射周惠达商量事情,周惠达不能应对,请求外出商议,返回后则说得头头是道,正中宇文泰下怀。宇文泰就问他出去同谁商议的,周惠达告知是苏绰,并顺着宇文泰的问话,推荐苏绰有“王佐之才”。由此,苏绰的名声再次上达最高当局。但重视归重视,并未当面恳谈,宇文泰依然把苏绰当做文人看待,令其转任著作佐郎。
宇文泰真正开始赏识苏绰,是在一次去昆明池观鱼的途中。昆明池在长安城西,是汉武帝时开凿的,附近有不少西汉古迹。宇文泰问周围大臣相关历史典故,谁也说不清楚。有人提议,苏绰“博物多通”,让他来解释。这一下,苏绰得到了进言机会,滔滔不绝,从“天地造化之始”,到“历代兴亡之迹”,侃侃而谈,应对如流。宇文泰听得高兴,竟然放弃了钓鱼,说了一路。回府后还不尽兴,留下苏绰,君臣对话,通宵达旦,很有点像秦孝公见了商鞅那样。“留绰至夜,问以治道,太祖卧而听之。绰于是指陈帝王之道,兼述申韩之要。太祖乃起,整衣危坐,不觉膝之前席。语遂达曙不厌。”天亮上朝后,宇文泰立即任命苏绰为大行台左丞,参典机密。此时,宇文泰的上面还有一位名义上的西魏皇帝,他以大将军兼宰相的身份掌控实权。苏绰的职务,相当于宰相府的办公厅主任。
苏绰在西魏中枢,一开始并未大刀阔斧全面改革,而是先整顿行政管理,建立规范的制度和流程。据史书记载,他这期间做的主要工作为“始制文案程式,朱出墨入,及计帐、户籍之法”,即建立公文制作与运行处理规范、财物账簿记录核算规范、户籍租税管理规范。这些制度,具有国家管理之基础建设的性质。虽然苏绰的具体措施已经不得其详,然而就凭财务记录用黑色表示收入、用红色表示支出这一创举,就可看出其价值所在。没有对行政管理的丰富经验和缜密思考,是无法想到这种记账方法的。其后,苏绰参与制定了西魏与东魏北齐对抗的重要军事决策,因功封爵,食美阳县五百户,职务也被提升为大行台度支尚书,领著作,兼司农卿,主管财政、文化、农业。
宇文泰来自鲜卑少数民族,出身于武川军人,他以尚书仆射出掌关西大行台起家,最终以大将军兼尚书令执掌西魏大政。在同东魏、南朝的拼争中,宇文泰本来处于劣势。但他励精图治,国势日兴。西魏刚刚建国的大统元年(535年),宇文泰就着力刷新政治,革除旧弊。“太祖以戎役屡兴,民吏劳弊,乃命所司斟酌今古,参考变通,可以益国利民便时适治者,为二十四条新制,奏魏帝行之。”(《周书·文帝纪》)经过十年积聚,西魏在国力上已经可以同北齐南朝争锋,号称“中兴”,而且最终形成了一整套新的制度体系,这套制度体系的文本是苏绰整理的。大统十年(544年),“魏帝以太祖前后所上二十四条及十二条新制,方为中兴永式,乃命苏绰更损益之,总为五卷,颁于天下。于是搜简贤才,以为牧守令长,皆依新制而遣焉。数年之间,百姓便之。”(同上)
真正展示苏绰治国才能的,是他在宇文泰改革期间提出的“六条诏书”。这六条诏书,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治国方略框架。“太祖方欲革易时政,务弘强国富民之道,故绰得尽其智能,赞成其事。”(《周书·苏绰传》)从整体来看,苏绰的“六条诏书”,是宇文泰战略定位的实施方案及其原理阐释,详见后文。
关于西魏北周时期宇文泰稳定社会、发展经济的措施,学界已经多有介绍,在此不赘。值得注意的是其文化方面的“顶层设计”。读史稍微细心一点就可发现,从西魏到北周,有一个在历史上很少见的现象,即整个国家体制包括官职设置,几乎全部按照《周礼》一书操作。例如,魏晋南北朝的其他国家,都已经在官员品秩上实行九品等阶。唯独北周推行“九命之典”,一品官称九命,九品官称一命,以此类推。流外官也分为九秩,九为最高,一为最低。州郡名称,大都改动,能复古尽量复古。尤其是官职体系,西魏本来实行三省制,其政务中枢行台是行尚书台的简称。而宇文泰放着魏晋以来形成的三省制不用,硬要仿照“周官”改为六卿制,宇文泰自任大冢宰,下面并列有大司徒、大宗伯、大司马、大司寇、大司空。初涉历史者往往对此很不理解,在官名上如此大费周折,是否有点小题大做?如果理解了当时的情势,就不难看出其中奥秘。南北朝时期,南方以华夏正统自居,诋毁北朝是“索虏”,摆出一副以文明对抗野蛮的架势。来自鲜卑的宇文部落,急于洗刷自身的边塞胡族色彩,以同南朝争正统。前期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措施,不过是向中原学习而已;到北周建立的周官系统,则等于向天下宣布自己才是文明正统。宇文泰小名黑獭,带有浓郁的草原味道,但他非要说自己是神农炎帝后人。关中是西周的古都旧地,周制是中原的文化象征,宇文泰全盘重建周制,以此表明自己才是西周的真正传人。孔子当年以不能恢复周礼而遗憾,宇文泰则以把周礼变成现实而自豪。《周书·儒林传》的序言,贬损魏晋以来的学术背离儒学正道,独赞宇文泰“雅好经术”,称道他“求阙文于三古,得至理于千载,黜魏晋之制度,复姬旦之茂典”。苏绰的“六条诏书”,就是西魏重建周制的操作性方案。
从这一意义上看,苏绰的“顶层设计”分为三步走。第一步,是从具体的工作流程、文件处理规范、公文格式等方面入手,建立标准化的政府运作方式,甚至包括公文撰写的文字和语句,也都仿照《尚书》撰写,在官府形成符合“周制”的细节性习惯。第二步,是从政府的管理内容和政策准则入手,在推行“六条诏书”的过程中,建立新的为政准则和价值理念,在周制的旗号下,实现治国方略的政策性转变。第三步,是在前两步进展的基础上,渐次推进官制变革,稳扎稳打,逐渐形成一套新的政府体系。这三步从宏观看是前后分明的,但从微观看又重叠嵌合于一体。大体上,在苏绰进入西魏中枢后的前几年,主要配合宇文泰的“二十四条新制”从事第一步。数年后开始进行第二步的探索,以“六条诏书”的颁布为标志,刷新政治,全面展开。随着第二步的深化,宇文泰又出台了新的“十二条制”,第三步一点一点上道,固化并扩大已经取得的成果。整个大统年间,苏绰和另一位著名儒士卢辩按照周制改创体制,却不急于求成。到苏绰死时,第三步尚未结束,但整个体制变革已成不可逆转之势,于西魏北周的王朝更替之间最终告成。包括北周的国号“周”,也是这种“顶层设计”的结晶。从苏绰的从政实践看,三步走并不是走完第一步再开始第二步,走完第二步再开始第三步,而是交错循环推进,重在实效。
苏绰的这种“顶层设计”和操作方式,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演进上具有重大意义。他的思路是由上而下的,否则就不是“顶层”;但操作是由下而上的,否则就会使顶层变成空中楼阁。他的体系是建构的,否则就不是“设计”;但实施是逐步演化的,否则就会遇到习惯的反弹。
苏绰是一位天生的政治家,“绰性俭素,不治产业,家无馀财,以海内未平,常以天下为己任。博求贤俊,共弘治道,凡所荐达,皆至大官。”(《周书·苏绰传》)尤可称道的是,他与宇文泰君臣相得的程度可谓鱼水,史上罕见。“今太祖方欲革易时政,务弘强国富民之道,故绰得尽其智能,赞成其事。”“太祖亦推心委任,而无间言。太祖或出游,常预署空纸以授绰,若须有处分,则随事施行,及还,启之而已。”(同上)古代帝王信任下属的例子不少,但是像宇文泰这样,外出时把签过字的空白公文交给苏绰,一旦有事由他全权处理,回来只是看看就完事,这几乎相当于让下属代行帝王权力,古今少有。与苏绰获得的这种信任可以媲美的,恐怕只有前秦苻坚时的王猛算一个,其他都要逊色得多。所以苏绰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才干,施展自己的抱负。“绰尝谓治国之道,当爱民如慈父,训民如严师。每与公卿议论,自昼达夜,事无巨细,若指诸掌。”可惜的是苏绰积劳成疾,42岁就英年早逝。
苏绰去世,宇文泰恸哭不止,送其归葬武功。“太祖与群公,皆步送出同州郭门外。太祖亲于车后酹酒而言曰:‘尚书平生为事,妻子兄弟不知者,吾皆知之。惟尔知吾心,吾知尔意。方欲共定天下,不幸遂舍我去,奈何!’因举声恸哭,不觉失卮于手。”(《周书·苏绰传》)安葬之日,宇文泰以太牢为祭,并亲为祭文。苏绰虽然事业未竟而早逝,但从北周到隋唐指导国家治理的时代精神,是由苏绰确立的。史称:“太祖提剑而起,百度草创。施约法之制于竞逐之辰,修治定之礼于鼎峙之日。终能斫雕为朴,变奢从俭,风化既被,而下肃上尊;疆埸屡扰,而内亲外附。斯盖苏令绰之力也。”(《周书·苏绰传》赞语)正是在苏绰的辅佐下,在北齐、西魏、南梁的逐鹿中,宇文泰统领的西魏由最弱的一方迅速崛起,治理有方,政治清明,为后来的统一王朝奠定了根基。
“六条诏书”的管理思想解析
苏绰所制定的“六条诏书”,是为实现宇文泰强国富民的理想而提出的治国方略。其内容为“先治心,敦教化,尽地利,擢贤良,恤狱讼,均赋役”。这六项内容从其相互关系来看,“先治心”为纲领,“敦教化”为手段,“尽地利”是基石,“擢贤良”是工具,“恤狱讼”是扬善惩恶以辅佐教化,“均赋役”是社会公正以分配地利。六者互相关联,互相影响,构成一个整体。
在“六条诏书”构成的治理系统中,从其内容看,“先治心”具有统领性质,相当于一个人的大脑,它决定整个管理系统的价值导向。“敦教化”和“尽地利”,是治理系统的左臂右膀,一个是精神,一个是物质。“恤狱讼”和“均赋役”,是治理系统的左右两腿,一个用来惩恶扬善,支撑道德的公正,一个用来平衡负担,支撑经济的公正。“擢贤良”是政府体系的自身建设,用来构建治理实体。这六个方面互相配合,互相呼应,构成一个六边支撑,缺少任何一边,都会失衡。
“六条诏书”的行动逻辑顺序,又与概念逻辑顺序不一样。“先治心”是观念领先,符合人类行为由意念主导的一般规律。而人类不能生活在真空里,物质需求是最原初的人类动机,因此,又需要“尽地利”以行动领先。由此,决定了“六条诏书”在实施中要以“先治心”和“尽地利”作为国家治理的切入点。在由“治心”引发的教化过程中,以“恤狱讼”救治道德的失落和鼓励人心的善念;在“尽地利”的过程中,以“均赋役”平衡物质的配给和调整需求的不同。以“正心”为前提,按照推行教化和劝课农桑的需要,形成贤良的选择标准和选择方法,又反过来依赖国家选拔出的贤良去审理狱讼,平均赋役。如此实现六边结构的运转,而且使其圆融无碍。
苏绰的“六条诏书”与一般的诏书相比,有着很大的不同。所谓诏书,是皇帝下达命令的文告,无须说理。苏绰拟定的“六条诏书”则全是说理式解释,而不是简单的下达命令。他对“六条诏书”的每一条,都要讲清其中的道理,说明其中的缘故,力争使上到天子下到吏员都能理解相关的意义。总体上看,“六条诏书”与其说是经皇帝批准下发的中央文件,不如说是经皇帝同意颁布的为政纲要兼辅导大纲。也许,中国历史上的官方辅导宣讲材料,就是从苏绰开始的。“六条诏书”的具体内容如下(引文均见《周书·苏绰传》)。
先治心
“先治心”强调意识的统领作用。苏绰认为:“心者,一身之主,百行之本。心不清净,则思虑妄生。思虑妄生,则见理不明。见理不明,则是非谬乱。是非谬乱,则一身不能自治,安能治民也!是以治民之要,在清心而已。”这就给出了把“治心”列在首位的理由。人的行为是由意识主宰的,“治心”的要害是清静。心思紊乱,胡思乱想,就难以辨明事理;不讲道理,是非谬误,则连自身都无法管好,谈何治民治国?
再进一步,苏绰指出,“治心”的关键在清静,即清除各种杂念,保持虚空静灵,防范邪念歪理的侵入,其重点在明是非,而不在彰善恶,尤其是“夫所谓清心者,非不贪货财之谓也,乃欲使心气清和,志意端静”一语,说明苏绰所说的“治心”,同此前的儒家尤其是思孟学派的“治心”不大一样,苏绰更重虚静,思孟更重诚意。苏绰的“治心”之说,跳出了性善性恶之争,更接近道家和释家。从苏绰写过《佛性论》以及当时佛教的流行情况来看,他对佛学是有了解的,所说的“治心”采纳了佛学中的思路。但是,他又不是纯粹的佛教徒,“治心”的目的不是完善自己的道德,而是清空心绪以防范偏见,形成不偏不倚的行为。“心和志静,则邪僻之虑,无因而作。邪僻不作,则凡所思念,无不皆得至公之理。率至公之理以临其民,则彼下民孰不从化。”由此,他完成了由“治心”到“治民”的逻辑论证。“治心”与“治民”,是体与用的关系,也是本与末的关系。“凡治民之体,先当治心”;“治民之本,先在治心”。这一论证,尽管仍然很粗略,但已经开创了后代心学的先声。
“治心”是为了治民治国,所以,就不能停留在佛家式的修行阶段,而要由心及身,以身作则。“治心”接着就要“治身”。“凡人君之身者,乃百姓之表,一国之的也。表不正,不可求直影;的不明,不可责射中。今君身不能自治,而望治百姓,是犹曲表而求直影也;君行不能自修,而欲百姓修行者,是犹无的而责射中也。”苏绰在这里暗含的前提是官员为百姓表率。这一点,又回归到儒家的经典主张。道家和法家以及其他学派,都缺乏统治者以身作则的主张,只有儒墨两家,才强调率先示范。苏绰的推论方式是,只有“心如清水”,才可“形如白玉”,而只有白玉之身,才可垂范社会。对于如何垂范,苏绰指出,应当“躬行仁义,躬行孝悌,躬行忠信,躬行礼让,躬行廉平,躬行俭约,然后继之以无倦,加之以明察”。一口气说了六个躬行,加上“无倦”和“明察”,是引导民众的八大要点,“行此八者,以训其民”。如此,则百姓对官员,自然会敬佩热爱,当作楷模而追随效仿,可以形成无需教训的教训,不待管理的管理。从思想渊源上看,六个躬行,全部是儒家的伦理标准,只有为了实现六个躬行的“无倦”和“明察”,透露出墨家和法家等其他思想的踪迹。可见,苏绰的价值取向以儒家为主导,而儒家以外的其他思想,更多地是被他拿来作为实现儒家理想的工具。
如果真正实现苏绰所说的由“治心”到“治身”的修炼,那就与圣人相差无几。但现实中很难做到。人人皆可以为尧舜,不等于人人肯定能成尧舜。所以,苏绰强调,国家应该在地方亲民官中率先推行“六条诏书”。州县守令管辖一方,相当于古代诸侯,秦汉以来的帝王每每强调与优秀守令共治天下。“明知百僚卿尹,虽各有所司,然其治民之本,莫若宰守之最重也。”只要亲民官能够心身正派,国家大局就安然无恙。
敦教化
苏绰强调,教化是人类特有的管理方法。所谓天地之间人为贵,就是指人类具有“中和之心”和“仁恕之行”。与木石相比,人有意识,与禽兽相比,人有伦理,所以为贵,可以走向文明。但是,文明也可以转向野蛮。“性无常守,随化而迁。”人性的外显是不固定的,就看如何习染转化。“化于敦朴者,则质直;化于浇伪者,则浮薄。”社会的淳和安详,来自于人性的质直之化;社会的衰弊败坏,来自于人性的浮薄之化。“治乱兴亡,无不皆由所化也。”从人性出发,苏绰论证了教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。在这里,苏绰的暗含前提是人性可以通过教化而改变。
针对当时的实际,苏绰认为,汉末以来世道丧乱、社会凋弊已经几百年,南北朝的内讧大乱也已经二十载,兵连祸接,刑罚严酷,百姓处于水火之中。“民不见德,唯兵革是闻;上无教化,惟刑罚是用。”西魏的中兴刚刚开始,天下的大乱尚未平定。战争和饥馑陷民于困苦,草创中的西魏政权只能权宜变通,所以“礼让弗兴,风俗未改”,有待于用教化方式移风易俗。当然,实施教化要有基础。苏绰遵循管仲“仓廪实则知礼节,衣食足则知荣辱”的思路,要求各地长官根据当地实际,“年稍登稔,徭赋差轻,衣食不切,则教化可修矣”。在这里,苏绰不主张冒进,而是明确把推行教化放在经济条件和社会秩序好转之后。
苏绰还从细节上对“教”和“化”进行了区分。“化”是潜移默化,在不知不觉之中进行的。“夫化者,贵能扇之以淳风,浸之以太和,被之以道德,示之以朴素。使百姓亹亹,中迁于善,邪伪之心,嗜欲之性,潜以消化,而不知其所以然,此之谓化也。”但是,潜移默化和加意诱导是相辅相成的,任其自然就不是“化”。在这里,苏绰又同道家划清了界线,他所说的“化”,要用儒家纲常伦理来濡洇感染,使民在不知之中化掉邪念贪欲。“教”是有意为之,在自觉自愿之中进行的。“教之以孝悌,使民慈爱;教之以仁顺,使民和睦;教之以礼义,使民敬让。慈爱则不遗其亲,和睦则无怨于人,敬让则不竞于物。三者既备,则王道成矣。此之谓教也。”通过孝悌教育增进慈爱,实现亲戚互助;通过仁顺教育增进和睦,消除社会戾气;通过礼义教育增进敬让,防范社会竞争。这是典型的儒家王道仁政主张。
苏绰特别指出,教化手段不仅能够“移风易俗,还淳反素”,更重要的是可以实现社会自治,体现无为而治的真谛。“垂拱而治天下以至太平者,莫不由此。”这种并非来自道家而更加倾向儒家的无为而治思想,特别值得统治者重视。
尽地利
苏绰认为,教化固然重要,却不能先行。如果缺衣少食而推行教化,只会无功而返。“人生天地之间,以衣食为命。食不足则饥,衣不足则寒。饥寒切体,而欲使民兴行礼让者,此犹逆坂走丸,势不可得也。”所以,圣王治国,必须先足衣食,后行教化。先足衣食,则从“尽地利”开始。
所谓“尽地利”,即劝课农桑,责任在地方的牧守令长。民众是参差不齐的,地方长官必须假定民众智力不足,不加督促就不会尽力耕作。否则,政府就会失职。劝课之法有三:首先是不失农时。每到春季,地方长官要督促部民,不论老幼,只要能操持农具,一律下田耕作,勿失其所。其次是持续中耕。一旦“布种既讫,嘉苗须理,麦秋在野,蚕停于室”,则需要不断打点料理。伺弄稼禾桑蚕,要像救溺救火,高度重视;面对水旱病虫,要像盗寇将至,全力对付。在整个生产过程中,做到“少长悉力,男女并功”,直到最后收获在手,“使农夫不废其业,蚕妇得就其功”。第三要警诫耕作不力者。对于“游手怠惰,早归晚出,好逸恶劳,不勤事业者”,由乡长里正报告郡县,郡县守令随事加罚,做到惩一劝百,砺勤诫懒。
在具体操作上,州县长官除高度重视农桑外,还要解决一些农户自己无法克服的问题。一是倡导互助,“单劣之户,及无牛之家,劝令有无相通,使得兼济。”二是技术培训,“三农之隙,及阴雨之暇,又当教民种桑、植果,艺其菜蔬,修其园圃,畜育鸡豚,以备生生之资,以供养老之具。”这已经很接近服务性管理理念了。
苏绰认为,劝课农桑是国家的根本,但农桑的主体是民众,官府必须处理好积极引导和民众自主的关系。劝课行为并不是越多越好,也不是放任自流。“为政不欲过碎,碎则民烦;劝课亦不容太简,简则民怠。”善于政务的明智长官,应该做到“消息时宜而适烦简之中”,不刚不柔,不烦不简,这种尺寸拿捏,必须恰到好处。
擢贤良
苏绰认为,百姓要靠君主来治理,君主要靠官吏来辅佐。“上至帝王,下及郡国,置臣得贤则治,失贤则乱,此乃自然之理,百王不能易也。”能不能选择贤良,关系到治乱安危。
对于官吏选拔,苏绰一一列举了当时存在的弊端,并提出治理方案。首先,他反对门资。魏晋时期的“九品中正制”,造就了门阀政治,上品无寒门,下品无势族。苏绰认为,“官二代”问题,是抑制人才的关键。他反复陈述门资妨贤的道理,“夫门资者,乃先世之爵禄,无妨子孙之愚瞽。”高门大户固然有卓异,但也有弱智。“若门资之中而得贤良,是则策骐骥而取千里也;若门资之中而得愚瞽,是则土牛木马,形似而用非,不可以涉道也。”所以,苏绰不是一概反对“官二代”,而是强调要打破门资限制。“今之选举者,当不限资荫,唯在得人。”如果有合适的人才,则从奴婢到卿相也未尝不可,古代的伊尹、傅说就是如此;如果是纨绔子弟,那么就是天子的后代也不能任用,古代的丹朱、商均就是如此。
其次,苏绰强调用人要以德统才,在德才之间先看品德。魏晋以来,与高级官吏看重门资相伴随,基层吏员则看重刀笔技能,“末曹小吏,唯试刀笔,并不问志行。”而刀笔技能与人品志向无关,技能卓越者,固然有志向高远的君子,但也有虚伪奸诈的小人。“若刀笔之中而得志行,是则金相玉质,内外俱美,实为人宝也;若刀笔之中而得浇伪,是则饰画朽木,悦目一时,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。”选拔官吏固然要考察材艺,但考察材艺是为了治民,“若有材艺而以正直为本者,必以其材而为治也;若有材艺而以奸伪为本者,将由其官而为乱也,何治之可得乎。”所以,苏绰强调在考察材艺之前先看志行。“其志行善者,则举之;其志行不善者,则去之。”由此,苏绰力图纠正魏晋以来战乱之中不问德行唯才是举的倾向,确立“德为才之帅,才为德之资”的用人准则。
再次,苏绰分析了人才的时代性问题。许多人认为当今之世缺乏贤能,苏绰不以为然,认为用人要“引一世之人,治一世之务”,后代不需要前朝人才,魏晋不能靠萧何曹参再世。人才的分布并不偏好古代,不过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人才标准而已。孔子曾言“十室之邑,必有忠信如丘者”,偌大一个国家岂有缺乏人才之理。所谓缺乏人才,其实质是“求之不勤,择之不审,或用之不得其所,任之不尽其材”,为选拔失误辩解开脱。
针对人才选拔的种种问题,苏绰提出了在任用中鉴别人才的操作方法。“夫良玉未剖,与瓦石相类;名骥未驰,与驽马相杂。及其剖而莹之,驰而试之,玉石驽骥,然后始分。”用现在俗话来讲,苏绰强调是骡子是马先拉出来遛一遛。在没有使用之前,是分不清贤良和庸碌的。历史上,姜太公在成名前屠钓,百里奚在得志前放牛,宁戚敲着牛角唱歌,管仲曾经三战三败。在这种当口,众人谁说他们是贤良?只有当他们功成名就之后,众人才异口同声说他们是奇才。所以,贤良的选拔,要“任之以事业,责之以成务”。如果要有了姜尚才任用,有了管仲才器重,那就永无姜尚和管仲的出头之日。世界上没有“未任而已成,不用而先达”的英雄。只有明白这个道理,才可以选贤任能,治理天下。求贤并非只有一种方法,也不仅有一条途径,但方法再多,途径再广,其本质无非是“任而试之,考而察之”。
最后,在任用贤良时还要注意省官简政。民谣称:“官省则事省,事省则民清;官烦则事烦,事烦则民浊。”官员精简,职责分明,则其人的能否立显,善恶易辨。官冗事烦,滥竽之徒就会混迹其中难以分辨。所以,“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。官省,则善人易充,善人易充,则事无不理;官烦,则必杂不善之人,杂不善之人,则政必有得失。”官职愈多,事务愈繁,扰民之举就会愈演愈烈。尤其是基层,那怕是闾正里长,也需要正人君子。乡里是国家的地基,基不倾斜,上者必安。
恤狱讼
司法的作用在于赏善罚恶,一旦赏罚不当,则适得其反,所以必须特别谨慎。“赏罚得中,则恶止而善劝;赏罚不中,则民无所措手足。民无所措手足,则怨叛之心生。是以先王重之,特加戒慎。”苏绰对司法提出了三个层次的衡量尺度。
司法的最好状况是以戒慎的态度对待狱讼,治狱之官要做到“精心悉意,推究事源”。先用“五听”查明案情,再以证验核实“五听”。所谓“五听”,出自《周礼》,指从辞、色、气、耳、目五个方面观察案情曲直。“一曰辞听,观其出言,不直则烦;二曰色听,观其颜色,不直则赧然;三曰气听,观其气息,不直则喘;四曰耳听,观其听聆,不直则惑;五曰目听,观其眸子视,不直则眊然。”(《周礼·秋官·小司寇》注)即观察言辞是否耐烦,说话是否脸红,气息是否匀称,听话是否疑惑,眼神是否慌乱。“五听”所得,是对狱讼曲直的初步判断,然后要以证据检验,务求实情。做到“妙睹情状,穷鉴隐伏,使奸无所容,罪人必得。然后随事加刑,轻重皆当”。
最好的司法,不仅要做到情真事实,不枉不纵,而且要心怀怜悯,慈悲为怀。“赦过矜愚,得情勿喜。”对于性质不同的罪错,赦免过失,矜惜愚昧。不为查明案情而兴奋,而为社会危害而负重。所以,审理狱讼还要分析案件不同情理,灵活掌握礼法条规,“又能消息情理,斟酌礼律,无不曲尽人心,远明大教,使获罪者如归。”达到这种水平,才是司法的“善之上”。
司法的第二层次,是虽有不当,却通情达理。地方长官良莠不齐,不可能人人都是神探高手;案件证据和信息也不可能完整无缺,推理求情经常会遇到障碍。在这种情况下,司法之人首先要持有公正理念,坚持原则,去除曲意偏袒之心,务求平允恰当之判,穷尽可以追查的线索;然后按照法律规定的范围用刑拷问,案情有疑则从轻不从重,未经审讯则不妄加处罚,根据情理做出推断,不因难以审理而积压案件。“率至公之心,去阿枉之志,务求曲直,念尽平当。听察之理,必穷所见,然后栲讯以法,不苛不暴,有疑则从轻,未审不妄罚,随事断理,狱无停滞。”能够做到这些,也算“善之次”。
司法的最坏情形,是长官没有仁恕之心,靠严刑酷法审理案件,把百姓当作草芥木石,甚至以能用酷刑为乐。是非颠倒,宽宥奸诈机巧之徒,惩罚朴实厚道之民。这种地方长官,只会制造社会矛盾,引发社会对立。“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残暴,同民木石,专任捶楚。巧诈者虽事彰而获免,辞弱者乃无罪而被罚。”这是最下等的司法,这样的官员是朝廷之害,决不能对他们寄有任何“共治”的希望。
苏绰认为,选择地方官员,以达到第二层次为基准,而且其人要在实现第二层次的基础上追慕上善,孜孜以求。一旦有最坏情形出现,则罪在不赦,朝廷决不能心存矜悯,而要以严刑伺候。
苏绰还指出,狱讼不仅仅是司法,更是德治。作为司法官员,必须“深思远大,念存德教”。古人的法制宗旨是:“与杀无辜,宁赦有罪;与其害善,宁其利淫。”就是说,在未能查明案情的情况下,宁可放过坏人,也不残害好人。但是后来的司法背离了古人的宗旨,“今之从政者则不然。深文巧劾,宁致善人于法,不免有罪于刑。”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,不见得都是因为司法官员滥杀无辜,而是因为官员的私心作怪。这种私心要么是为了追求政绩,要么是为了避免后患,所以官员宁枉勿纵,宁酷勿循。苏绰对此严加指斥,“此则情存自便,不念至公,奉法如此,皆奸人也。”从最一般的道理上讲,人死不可复生,然而因酷刑毒楚、屈打成招、畏刑自诬而送掉性命者,古往今来不在少数。古人为此设有“五听三宥”之法,规范明慎庶狱之典,以彰爱民之意。“五听”已见前述,所谓“三宥”为:“一宥曰不识,再宥曰过失,三宥曰遗忘。”三宥之外,还有三赦:“一赦曰幼弱,再赦曰老旄,三赦曰惷愚。”(《周礼 · 秋官·司刺》)以三宥三赦,体现用刑之厚道。苏绰还以汉代以来的“天人感应”说,解释司法不公的恶果。“凡伐木杀草,田猎不顺,尚违时令,而亏帝道;况刑罚不中,滥害善人,宁不伤天心、犯和气也!天心伤,和气损,而欲阴阳调适,四时顺序,万物阜安,苍生悦乐者,不可得也。”正因为司法重要,苏绰特意引用谚语说:“一夫吁嗟,王道为之倾覆”。用当今的语言讲,就是只要有一个案件不公,正义就不复存在。从另一方面看,只要有败德行为未受到惩罚,司法就未达到立法本意。“若有深奸巨猾,伤化败俗,悖乱人伦,不忠不孝,故为背道者,杀一利百,以清王化,重刑可也。”把握了这两个方面,司法中的政治就完善无遗。
均赋役
赋税和徭役是国家生存的基础。苏绰所面临的情况是,国家尚未统一,战争正在进行,民众负担不可能削减下来,然而,却可以做到更为平均。孔子曾经说过,“有国有家者,不患寡而患不均,不患贫而患不安。盖均无贫,和无寡,安无倾。”(《论语 · 季氏》)对“均无贫”如何理解,是“均赋役”的关键。苏绰指出,“夫平均者,不舍豪强而征贫弱,不纵奸巧而困愚拙,此之谓均也。”也就是说,平均不是拉平赋役负担,而是平等对待下民。
“均赋役”的前提是“尽地利”。地方长官要以劝课农桑来务本,而不仅仅是以完成赋税为业绩。没有财货,赋税从何而来?而财货的生成积累是一个长期过程。优秀的地方长官,不在于其征收及时,而在于其事先经营。“财货之生,其功不易。织纴纺绩,起于有渐,非旬日之间所可造次。必须劝课,使预营理。绢乡先事织纴,麻土早修纺绩。先时而备,至时而输,故王赋获供,下民无困。”有了充足的前期功课,赋役就不会对民生造成重大影响。怕就怕缺乏前期工作,临时征发,只顾当下,剜肉补疮。尤其是长官为了完成上命,推卸自己的责任,不落稽迟之失,依赖笞杖刑罚催科,陷小民于困境之中。民无蓄积,捶扑之下,富商大贾乘机牟利,不是抬高贡赋品价格,就是催生高利贷债务。“有者从之贵买,无者与之举息”。真正承担赋役的百姓,被官府和商贾两头切割剥夺。民生的凋敝,大都与此有关。
生产组织到位,民间蓄积充实,还要在赋税收缴时均衡负担,在徭役征发时用心调度。租税征收固然有基本规范,然而收缴顺序的排列,民间贫富的掌控,需要认真盘算。“租税之时,虽有大式,至于斟酌贫富,差次先后,皆事起于正长,而系之于守令。若斟酌得所,则政和而民悦;若检理无方,则吏奸而民怨。”有些地方官员,认为收缴租税中的具体事务属于乡长里正,官府办理自有掾属小吏,无关行政长官,这就可能导致基层作奸舞弊,吏胥乘机自肥。长官应当斟酌调停民众的税务矛盾,监控敲打乡官吏胥的行为。徭役的安排也类似。“又差发徭役,多不存意。致令贫弱者或重徭而远戍,富强者或轻使而近防。”同样征徭服役,两个月的徭役,地点远近不同,对民众生活的影响大不一样。同样为官府承担劳务,轮班站值和运送重物,劳累程度大不一样。这也需要长官恰当调度,合理安排。在“均赋役”方面,具体做法可能千差万别,但总体上,需要守令心怀公正,怜恤小民,谨防倚强凌弱,坑害贫贱。
苏绰对“六条诏书”给出的详细解释,成为西魏北周的政务指南。“太祖甚重之,常置诸座右。又令百司习诵之。其牧守令长,非通六条及计帐者,不得居官。”正是这“六条诏书”,为西魏和后来的北周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体系。在管理思想上,“六条诏书”兼容儒墨道法各种学说,以崇尚周制并切合西魏现实作为治国总纲,以提纲挈领的宏观视野和细节操作的具体规范相结合,在帝制时代的治道探究上做出了新贡献,也为后来的宰相之道树立了一个新样板。
汉唐之间的善治桥梁
苏绰其人,除非专业治史者,一般人不大注意,其原因可能很多。首先,西魏在历史各个朝代中不像汉唐那么有名;其次,苏绰对西魏的功绩又被宇文泰的光芒所掩盖;再次,苏绰本人也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故事传说;最后,苏绰的工作过于琐细呆板。这些原因整合到一起(也许还不止这些原因),致使苏绰不为大众所知。
然而,在从秦汉到隋唐的管理思想演变中,苏绰是不可缺少的一环。汉代在管理思想上形成了三纲六纪的礼法之治,唐代在管理操作上完善了帝制时代的治理之术,而由汉到唐的过渡,其间的转化是由苏绰启动的。
从思想渊源上看,苏绰很杂,至今还有学者为把苏绰思想归入儒家还是归入法家争得不亦乐乎。隋代王通也肯定苏绰为“俊人”,但比不上辅佐苻坚的王猛,认为苏绰之道“行于战国可以强,行于太平则乱矣”(文中子《中说·天地》),其原因就在于苏绰称颂申韩之学,施行法家之治。当代学者陈寅恪对苏绰的思想评价不大高。他也承认苏绰“为宇文泰创制立法,实一代典章所从出”。宇文泰基于建立文化自信,以关中为本位与山东和江陵抗衡,苏绰适应了这一需求。陈寅恪认为,苏绰“依托关中之地域,以继述成周为号召,窃取六国阴谋之旧文缘饰塞表鲜卑之胡制”,即依赖关中家族的学问传承,以《周礼》为范本托古改制,把战国诸子的思想揉合杂拌,从而把鲜卑胡制与华夏文化结合为可操作的治理结构。然而,就其学说来讲,“非驴非马,取给一时,虽能辅成宇文氏之霸业,而其创制终为后王所捐弃,或仅名存而实亡,岂无故哉!”(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)说他非驴非马也好,说他缘饰胡制也好,都佐证了他把不同学术(主要是儒术)拿来用于辅佐宇文泰得天下,而且取得了成功。陈先生的批评,主要出于对其学术的看法。苏绰杂取各家,不仅表现出受到先秦诸子的种种影响,而且还受到当时流行的佛学和玄学的浸染,他又没有什么学术创见,顶多是长在对策参谋而已,“阳传周礼经典制度之文,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”,以学术为志业的陈先生当然看他不起。
对苏绰评价最高的,莫过于南宋叶适。叶适以创立重视事功的永嘉学派而驰名,最反对陋儒空谈心性,开经世致用之先河。苏绰虽无学术创建,却能把学术思想创造性地用于国家治理,这当然正对叶适的胃口。所以叶适认为,苏绰的历史贡献直追管仲,即便孔子复生也会把赞扬管仲之语移于苏绰。尤其是以《周礼》为模板建构治国方略的,历史上总共只有三个半人,三个分别是王莽、宇文泰和宋神宗赵顼,剩下半个是仿照《周礼》名号立国的武则天。真正成功的,只有宇文泰一人。宇文泰之前,可参考的仅仅是王莽,而王莽推行周制的效果并不好,搞得天下大乱。苏绰的历史贡献,就是把宇文泰的想法落到实处,从大乱中走向大治,这样的事功更是难能可贵,所以叶适格外重视。
苏绰能够成功,一个常人不大注意的原因是他之琐细。他从公文规范和行政流程入手,以其“计帐术”而出名,甚至不厌其烦地制作公文样式,规定公文文体和词汇。这些琐细事项,往往是那些志向宏远的改革家看不上的。然而,正是这种琐细事务,在推行政策上大有裨益。苏绰管理思想给后人的启迪之一,就是架构性的整体变革,需要从细节性的操作习惯入手。
苏绰的儿子苏威,可以说得了其父真传,却没有收到其父之效。苏威是隋代大臣,其廉洁清俭,执著秉公,重视细节,与苏绰一脉相承。然而,虎父犬子,为人所轻。苏威的执著缺乏圆融,时人认为其“无大臣之体”;苏威也具体制作格令章程却过于烦碎,时人认为其“非简久之法”。苏绰的成功经验,到了儿子苏威手里就变成了失败教训。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苏威与苏绰相比,父子面临的情境有了根本变化。苏绰的文案程式和计帐之术,是为推行宇文泰的整体改革而做的铺垫;苏威的格式规范和办事章程,是撇开隋朝已经统一追求稳定的大局而重视细节的变革。苏威不如其父的关键,在于重视细节而忘了大局。细究“六条诏书”,不难发现,苏绰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大处着眼,小处着手。苏绰管理思想给后人的启迪之二,就是细节要和大局互相关照;而且苏威的教训还说明,即便是十分成功的经验,也不能无条件移植。
宇文泰的变革,单纯从表象看并不持久。如按照《周礼》设计的官制,到北周的后期就开始放弃,进入隋代后就不再施行。很多人以苏绰之法未能持久而加以批评。对此,陈寅恪倒比较公正,他的观点是:宇文泰和苏绰,“正以其并非徒泥周官之旧文,实仅利用其名号,以暗合其当日现状,故能收摹仿之功用,而少滞格不通之弊害。终以出于一时之权宜,故创制未久,子孙已不能奉行,逐渐改移,还依汉魏之旧。”(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)但陈先生忽略了学术与政策的不同,学术志在传世,政策志在适用。唐玄宗时期的名相姚崇,曾经问中书舍人齐浣,自己作为宰相,可以与谁相比?比古代名相管仲、晏婴如何?齐浣答道:“管、晏之法虽不能施于后,犹能没身。公之为法,随复改之,似不及也。”显然,齐浣看不上姚崇,但为了给姚崇留点面子,最后说:“公可谓救时之相耳”。姚崇对此评价反而十分得意,说“救时之相,岂易得乎!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11,开元三年正月)。由此可见,在政策评价中,救时比传世更重要,权宜比坚守更迫切。宇文泰和苏绰推行的周制未能持久,恰恰是因为随着北周的强盛,周制的使命已经完成。苏绰管理思想给后人的启迪之三,就是进行管理思想史研究,应当把学术评价和政策评价恰当区分。
苏绰当初在提出“六条诏书”时,其实就没有打算让他设计的具体措施传世,恰恰相反,他极希望随着时局变化而调整这些措施。根据《北史·苏威传》记载,苏绰设计西魏的税收方案,因为国用不足,所以税负较重。他曾经感叹说:“所为者正如张弓,非平世法也。后之君子,谁能弛乎?”儿子苏威牢牢记住了其父的心愿,到了隋朝,每以减轻赋税为己任。结果,苏威改变其父赋役制度的做法得到了史书称誉,而坚守其父文书格式的做法则被史书诟病。弄清这一点,对理解苏绰的管理思想有益,也提醒治管理思想史者,对传世和救时、理论和实用的关系,需要谨慎对待。
管理思想不同于哲学思想,它不仅要求学术性思辨,而且要求实用性操作。秦汉以来的帝制时代,不再有先秦诸子提出思想原典的学术高峰,而是企盼治理国家追求盛世的王朝辉煌。如何把学术性思辨和实用性操作贯通起来,成为管理思想发展的主题。董仲舒等人是从学术出发,由学术推及实务;诸葛亮等人是从实务出发,由实务反扣学术。到苏绰的“六条诏书”,实现了学术与实务的贯通,做到了“顶层设计”与基层操作的呼应,这正是苏绰的贡献。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