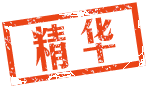壹
马腾做梦也想不到,自己那个威震西凉,数次拒绝丞相辟举的儿子马超,竟然在曹军讨伐汉中张鲁之时,联合关中一众势力,教这个荡平北方的丞相吃了大亏。他可以想到的是,身在邺城的一众家人亲从,怕是一个也活不成了。
这事还有转圜的余地么?早已被限制了自由的马腾,只得在府中来回踱步,想破了头也琢磨不出一个让家人脱罪的主意。
次子马休在一旁看着焦躁不安的父亲,偏也拿不出什么高明见识,暗自喃喃道:“大哥自己造了反,全然不顾父亲和兄弟族人的命了。现在大哥没能要了曹贼的命,又有夏侯渊在西线屯兵,我们这样受曹军监视……”
“够了。”马腾只是轻声喝断了儿子的话,为将时的嗓门与底气都似被他藏了起来,“曹操新胜归来,剑履上殿,整个朝廷被他攥得严实实的,那逆子认韩遂作父,哪曾把我这个亲爹放在眼中。”顿了一顿,又道,“现下里埋怨这些有什么用,举朝上下,怕是只有荀令君能教我如何解这死局了,可他偏偏又远在许都……”
“咱们被困着不能走动,连个府外的活人都见不到,鸟儿也飞不出,就算荀令君有主意又能如何……”马休接着吐了几句分辨不出的抱怨,却见三弟马铁匆匆从院外进来,喘着粗气,心中顿感不安。
马腾不等马铁说话,像是已经知道了什么,问道:“是不是曹操要对咱们动手了?”
马铁答道:“府、府外的人多了几倍,门外围了三层全甲的兵,曹贼怕是真要来拿咱们了,咱们与其坐以待毙,不如干脆……”
“干脆什么?以咱们府上几十人,要反这桶也似的邺城?”马腾嗤道,自嘲也似地淡淡说着,“咱们马氏一族,怕是要断在这邺城了。孟起这是有意害我,害他这些个兄弟啊……”
“卫尉大人可在?”
府门外传来这无比洪亮的一声,院内的树木仿佛都随之晃了晃。马腾已经知道来的是谁,反而没了先前那些慌乱,淡定地穿过庭院至府门口,拱手道:“武卫中郎将别来无恙。马某好大的面子,竟能让中郎将亲来迎接。”
马腾本已较常人高大,许褚竟比他还高出些许,那两条粗膀子胀得肩甲都显得有些上翘。不愧是能与我那逆子相抗的虎侯。马腾心中暗道。
许褚面上表情不变,一双牛眸般大小的眼睛直直瞪着马腾,嘴好像没怎么开合,声音就发自腹内般震荡出来:“卫尉大人说笑了,一个跑腿而已,大人就不要调笑了。”
马腾试探地问:“敢问武卫中郎将因何事带马某去何处?”
许褚从头到脚沉如铁塔,仿佛连衣角也没动过,闷声答道:“下官此来是护送卫尉大人一家至许都的,到了地方,自有司隶校尉钟大人与您解释。”
马腾叹了口气,苦笑无语。
贰
钟繇看着面前正悠然品茶的荀彧,实在佩服他似是对世间万事都能这般淡然处之;却又因自己现下这事,实在急得火烧眉毛,对方却仍不以为意,心中还是颇有些不满。
“啊……令君啊……”钟繇干笑一下,还是耐不住性子开口问道,“这马腾的事,您看……”
“钟大人,这可是头茬初制的武阳茶,当真不想尝一尝?”
“我的尚书大人呐,这马腾的事啊……”钟繇还想多说,却对上荀彧那双细而亮的眼,瞥见后者唇角似有若无的笑意,当下捧起茶碗,长袖掩着一饮而尽,“好茶!”
荀彧笑道:“钟大人本是风雅之人,好茶当品,可不像酒水那般饮啊。”他顿了顿,将茶碗向前推了推,双手置于膝上,正色续道,“卫尉这事,不难。”
“不难?”钟繇道,“丞相分明是要置马腾于死地啊,那马超在西边不晓得要搅出多大动静,如此一来,岂不是逼得他要更进一步嘛……”
“更进一步又将如何?”
“这……”钟繇被荀彧抢白,顿时语塞。“更进一步,就……是攻入雍州,进而威胁司隶腹地……”
荀彧像是没忍住笑出了声,道:“元常,元常啊,你实在是多虑了。马超领汉将军衔却起兵作反,本就叛于忠失于信,现在父亲胞弟又将因他丧命,更是个无父无君,不孝不义之人,天下将如何视之?他能掀起多大风浪啊。”
钟繇暗暗挠头。这荀令君儒雅端庄,就连说起话来也少有直来直去,但像今天这样云山雾绕不点正题的先例,实在是不多。
荀彧知钟繇疑惑,接着道:“妙才将军已经屯兵雍西,又有朱灵坐镇长安,我军已经稳固。先前一战两方都没占得太多便宜,马超以西凉一州之力与我军对抗,必不能久持。马腾若死,等若逼马超立即发兵再攻,而此时妙才将军与徐晃已经布防停当,料马超军势难有寸进,以他为人暴虐,久必生变,适时施以离间之计,西祸可解。”
“原来令君早有谋算。”钟繇叹服。心想世人只知道荀令君儒而雅量,却鲜有人见识过他杀伐决断,恨而无情的一面。
在荀彧看来,与马超交战需要耗,但又不能一味地拖延时间。一方面,凉州土地贫瘠,物产不丰,不能久战;另一方面,马超为人性急暴躁,刻薄寡义,西凉联军关系松散,实可分而化之。马腾一死,必会激得马超急切求战,在防守稳固的当下,只要让马超吃一次亏,就可加速西凉联军的分裂。
荀彧的谋划中,与敌相耗与逼敌急战非但不矛盾,反而相互辅成。而其中关键,便是卫尉马腾必须要死。
荀彧垂下头,先将煮水续入钟繇面前的碗中,又为自己的碗内加了水。“这茶与酒不同,初次入水口感苦涩却有回甘,二次入水则感口舌温润,三度入水而味淡爽口,其后便须换茶再品。不像酒水,何时饮来滋味都一般无二,倒会令人头脑发胀,想不明白事情。”说着,似有若无地瞥了钟繇一眼,“元常可是念及与马腾旧情,心有不忍呐?”
钟繇听了,脊背一凉,忙解释道:“这,令君说笑了,我督长安之时,确实与马腾韩遂有过接触,但行事布令均由德容着手,我与马腾并无私交,怎会因他念情呢。”
“张既张德容?”荀彧抬眼道,“德容确是能臣啊,有他在,可保雍州政事无虞。”
钟繇盯着座前新续了水的茶碗,暗暗思忖荀彧话中的意味。自己与荀彧相交多年,被他如此试探也似地问话,竟还是头一次。自从丞相剑履上殿,享有昔年董卓一般的特权之后,这个高深莫测的荀令君,似乎也发生了某些不可查的变化。
叁
当曹丕第三次将手中甘蔗拍在自己臂甲上,邓展终于不得不承认,眼前这个只二十许岁的青年,剑法确实在自己之上。
“五官中郎将艺法高妙,剑速绝伦,邓展佩服。只不知中郎将为何致胜的每一剑都打在末将手臂之上?”邓展将手里甘蔗扔在地上,插手问道。
曹丕捻了下并不浓密的胡须,慨然而笑:“邓将军可知一人,名唤王越?”
邓展愣了一下,随即应道:“可是建宁年间的虎贲将军,堪称剑神的大侠王越?”
曹丕道:“丕剑艺师从史阿,而史阿的老师,正是王越。”
邓展恍然悟道:“那是难怪了,王越剑法以快著称,史阿也是当世无双的快剑手,中郎将有这般剑速,看来已是深得史阿真传。”
“丕臂力不及老师,剑技速而力不沉,难以从中路击破邓将军的防守,所以只能迂回两翼,打将军的两条胳膊了。”曹丕掂了掂甘蔗,面露傲色,“这甘蔗也是极不趁手,实在比不上正经的宝剑。”
邓展也是以武闻名的将军,其剑势大开大合,又颇有些刀法的意味,平素武场上十数人近不得身。没想到与丞相之子比剑,竟然连输三阵,加上旁人哄笑,面子上实在有些过不去,便鼓起勇气,挑衅般地道:“五官中郎将自曝剑法短处,末将已有取胜的底气,中郎将可敢再与我较量一次?”
曹丕的傲气从脸上直溢到手中甘蔗的前端,哂笑道:“有何不可。”
“如此,末将得罪了!”
话毕,邓展抄起地上的甘蔗,就这么低着身子向曹丕冲去。
曹丕见邓展压低了身形,知道他有意掩着自己的两臂,若如先前一般打他两侧,邓展只需要将手向任一侧挑起,便能破了他的剑势。而快剑一旦被荡开,便会中门大露,到时邓展只需出一拳或踢一腿,胜负就会分明。
心念至此,曹丕脚下碾着碎步向后急退,待邓展冲势一老,立即向邓展左臂处刺出一“剑”。
邓展心道果然不出所料,向左旋了半个身,手中甘蔗向上一挑,两“剑”交击,竟也有一声脆响。可是这一挑却并没把曹丕的甘蔗荡开,邓展只道是自己使力不够,一气既老又生一气,追着曹丕兵器连打三下。
曹丕硬接了前两击,到第三下时手上却松了力,手上的兵刃顺着右手手腕滑落,人也侧腰半转,左手从背后接住甘蔗,脚下大步一迈,已然到了邓展背后。
邓展大惊,连忙转身,手上甘蔗不忘护着胸前。可就在他的脸完全转向曹丕时,后者手上的“剑”已经指在了他的眉心上。
“如何,邓将军,这回服了?”曹丕上挑的眼角和狡黠的唇边无不涌出得意之色,仿佛天地之间,再无一人能在剑艺上胜过他。
“五官中郎将剑法天下无对,末将这回真心服了。”邓展再次扔掉甘蔗,这回已是心服口服。
曹丕见了,满意地掸了掸长袖,道:“邓将军过奖了,丕剑法不敢说胜过老师,但若说是射术,敢称无敌于天下。”
“中郎将还精于箭射之术?”
“丕自小与渊叔学射,至一十六岁已经青出于蓝,就连令君老师都对我的射术赞叹有加。”声调愈高,愈显出曹丕的自傲,偏偏刚赢了以剑闻名天下的顶级高手,邓展并在座宾客无法也不敢说他什么。
邓展似是想起什么,压低声音对曹丕说:“中郎将,末将明日就要往许都去了,适才谈及荀令君……此次我欲与夏侯将军、董祭酒等联名保奏丞相晋公爵位,怕荀令君会有他意……”
曹丕瞪他一眼,示意不宜多说,随之道:“惇叔和董昭自会处理妥当,令君老师……应该……不会有问题吧……”
在剑法、射术与诗词文赋之外,天下比想象中更为广大。
肆
或许这许都城中有许多人能感觉到,荀令君似乎发生了些许变化,但大概只有荀攸能明白,这个比自己年龄还小些的叔父,内心已经苦闷到了何等地步。
荀攸已经将自己所得到的消息都说给了荀彧,见叔父听罢一言不发,似是陷入沉思,便也不打扰,就那么端坐着静等。
良久,荀彧终于开口:“公达,此事可有实在把握?”
荀攸心忖叔父贵为尚书令,人脉眼线自然不会比荀攸逊色,思虑许久却问出这么一句并无意义、要求确认的话,实在不像往日里的叔父。
“两月前董祭酒曾到我府上试探我,想来是要摸清我的意思,邀我一道进言。我装作不知推脱了。至昨日,已知清苑亭侯刘若、都亭侯王忠、将军邓展、刘勋、鲜于辅,甚至元让将军都在董昭的名单中。”荀攸道,语气平稳,并没有流露出多余的情绪。
荀彧又沉默了片刻,却岔开了话题:“西方战事如何?”
这一问,问得荀攸也意外地抬了下眼,随即应道:“妙才将军初始在马超手上吃了些亏,随即击破了其梁兴部,斩杀梁兴,两方暂时歇战。我已使人联络了韦康旧部杨阜等人,待时机成熟,便会起兵反攻马超。大概不出一年,西方战事就将有个结果。”荀攸之所以留在许都而没有随曹操回归邺城,也正因为他需要就近使人行分化之计。
荀攸又将自己为夏侯渊所设的部署一一说明,期间观察叔父的神态,感觉对方似乎在听,又似乎没有在听。他自己虽不长于武艺,但自小性格刚猛,敢于直言、甚至不畏与人动手。后经自己这位德才兼长、温润沉稳的叔父介绍到曹操麾下,与叔父共事多年,虽一主外一主内,平素见面时候并不多,但也从其身上学到了那种淡然与平和。这份淡然与平和,使他的头脑更加活络,对时局战机的把握也更加透彻。
若论天下善奇谋者,称荀攸为首应不为过。
从分化马超势力听到雍、凉、益三州局势的推演,荀彧终于开口。这一开口,却又把话头转向了一个荀攸不止一次想过,却任何人都不敢明说的事情上。
“公达,如果丞相依董昭进言,晋公爵位,你将如何?”
荀攸被这么猛一问,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。
荀彧却不等对方回应,神色发厉地继续道:“如果曹公登位,再上一步就会晋位为王,破了高祖异姓不王的成规,势成众矢之的。其时若荆扬益凉四州未定,又失了奉天子的高义,我军将再也无力征讨逆军,汉室也必将亡于曹公百年之后,这大汉的天下会被诸侯瓜分割据,自立为王称帝者众,以致重蹈战国覆辙!”
荀攸也曾设想过丞相为公后的种种影响,但听叔父这么一说,方感到事态发展将远超自己的假想。
“公达,我请你无论如何留在曹公身边,尽你所能护其周全。”荀彧语气前所未有地坚定,“即便僭越,曹公依然是汉室……唯一的依仗。”
这回轮到荀攸沉默了。
荀彧摇了摇头。“抱歉,公达。”他说,语气中去了那份坚定,又被无奈填满了,“我已半百,公达较我尚年长几岁……人,终究难敌天意啊。”
荀攸眼眶竟觉似要潮涌,忙抬手以袖擦去湿润,道:“叔父此言,我铭记在心。终我一生,定不负叔父,不负丞相!只是……”犹豫片刻,终于下了决心一般,压低了声音续道,“丞相会否篡汉而自立?”
荀彧眼中精光一亮,复又恢复如常,长叹道:“曹公,怕是要做周文王。”
荀攸何等聪明,一听便知道叔父话中意味。
“世人皆道董卓参拜不名、剑履上殿,作恶朝廷,不知昔年汉相萧何才是头一位享此待遇的人。忠焉奸焉,功焉过焉,本就是世人口中咀嚼,因所处地位、立场而变的东西。我荀彧一生,忠于家族,忠于曹公,忠于天子,忠于我大汉的大好河山。曹公今已位极人臣,若要再登高一步,我一定会出言反对,即使遭受忌恨也在所不惜。若是连我也赞同董昭一党,恐我煌煌大汉行至四百年间,举目四海也再难找出一个肯对天子尽忠的人了……”
荀彧说到此处,两人俱已热泪盈眶。
夕阳,终于向西边落去了。
伍
董昭看着在座诸位,一字一字道:“明日丞相东征大军将过许都,廷议时,我将重申五等爵位,进言丞相晋公爵位,咱们一直谋划的事,马上就要落实了。”
清苑亭侯刘若道:“这几个月奔走下来,军中多数人都会附议。”
董昭满意道:“我曾经探问过荀攸的意思,他和荀令君恐怕不会同意我们的主意。不过此等大事,料他们也不会当庭表示异议吧。”
“依末将看倒也未必。”邓展摇头道,“末将认为,荀令君一定会反对祭酒的进言,以荀令君在朝堂的地位与影响,祭酒还需想好应对之策才好。”
董昭笑道:“丞相平乱敌而复中原,十四州坐拥其九。光武之后,有谁能及丞相这般伟绩。兼之六月间天有日食,此乃旧朝黯淡,新朝将起之相,我们只需不把话挑得过于分明,任他荀令君如何巧舌,天理也在我们这方。”
见邓展还有疑虑,董昭挑了挑眉,颇为不满。他站起身来,缓缓走到邓展身前,问道:“邓将军还有思虑?”
邓展连忙起身施礼道:“末将不敢,终是谨慎些,想得万全些为好。”
董昭又笑出声来,这次的笑声中多了一番哂玩的意味。“荀令君只有一人之力,能有多大威胁。荀攸谋划西方战事,一把年纪又随军去了,能不能活着回来尚不肯定;程昱年纪更大,人也躲在邺城,轮不到他来争,更何况他也是倾向于丞相晋公爵位的;贾诩那老家伙倒是高深莫测,但你见他得罪过谁么?这种伤害主君意愿的事情哪是他能做出来的?”他斜着膀子,瞅着邓展,“邓将军,你说以我董昭今时在军中的地位,兼有元让将军帮腔,还愁大事不成?”
邓展只得再次施礼,“祭酒大人教训的是,末将没有疑义了。”
刘若在一旁圆场道:“邓将军也是多虑了,董祭酒怎会思虑不周呢。只不知祭酒认为,若封公国,位于何处才好?”
董昭抚着胡须,在府中踱起步来。“以我所见,冀州物产丰富,人丁兴盛,就以冀州十郡为封地,国都设在邺城,国号以邺城所在魏郡而称‘魏’,最好。”
都亭侯王忠附和道:“董祭酒果然高明,《尚书》载冀州乃我华夏九州之首,现在也只有豫州堪与其相提并论吧。” “豫州乃许都所在州域,自是不能奢想,”将军刘勋也应和着道,“确是没有比冀州更理想的了。”
董昭坐回位上,大为满意,长袖一挥,朗声道:“明日事成,董某和在座列位,都将是我魏国的开国元勋!”
众人轰然响应。
陆
曹丕毕恭毕敬地跪侍在荀令君床边,满身的傲气都藏进内心深处,脸上只映出关切之色。
“令君老师既然患病在身,就不要行这些道路来劳军了,应回许都安心休养才是。”曹丕略带埋怨地说。若说天底下有几个令他真心佩服的人,除了自己的父亲曹操,恐怕也只有荀令君了。
荀彧并没有看向曹丕,似是自顾自地道:“丞相此番征讨孙权事大。闻说那孙权改秣陵为建业,大有建都自立的意味。丞相年近六旬尚且亲自督军讨伐逆党,我这区区疾病又算得了什么。”
曹丕咬了咬下唇,问道:“令君老师可是对父相仍有怨意?”
荀彧喉中挤出莫可奈何的笑声,道:“我与曹公相交愈二十载,虽偶有政见不合,却从未有过私怨。”他转过脸来,望着曹丕,“子桓呐,论及剑法,鲜有人是你的对手;前日看你行猎,见你左右开弓而无虚发,射术犹胜昔日,更是无人能及;文章辞赋本就是你所长,自不必提……”
一阵咳嗽打断了荀彧的话,曹丕忙从侍从处接过唾壶,让荀彧咳出痰来,又要扶荀彧半坐,方便咳后饮水。
荀彧摇头,表示不用在意,接着说:“可若想治理这天下,光靠这些就不够用了。”他冲侍从摆了摆手,示意他们出去,此间便只剩下荀彧与曹丕两人。
曹丕心知荀令君在父相诸子中,或多或少地表露出对自己的偏爱,知道接下来的话可能对自己意义重大,自然强压下心中情绪,凝神静听。
“修兵法可以敌万人,习政要可以治郡县,可唯有洞察人性,知其长短,量才置人,方能以众将之兵戟统率千军,以能臣之刀笔安抚国家。子桓当牢记于心。”
曹丕心下一震。在他的印象中,一向儒学大家姿派的荀令君,从来也没有说过这番用人乃至御人之说。
几年未见,荀令君给他的感觉与之前全然不同。之前在朝堂之上,荀令君痛斥董昭,坚决反对父相晋魏公,之后便闭门谢客,直到此次到曲蠡之前,他没能和荀令君说上哪怕一句话。
“子桓啊。”
曹丕正困于自己的思虑之中,突被这一声轻唤惊醒,见荀令君双目微闭,呼吸均匀,显然是从刚才那阵咳嗽中舒缓过来了,忙应道:“令君老师,我在。”
“你父相的心意,其实始终未能定下来。”荀彧全无先例地,用对待亲子般的口吻对曹丕说,“古来王侯出征,世子监国,你可曾因此番征伐扬州,留守后方的不是你而愤懑?”
这回曹丕可是惊得冷汗都从背脊溢出来,如果发问的是父相,他肯定当时就跪拜下去,叩首否认了。
荀彧睁开了眼,慈爱地看着曹丕,口中说出的话可是怎也与“慈爱”无关:“子桓呐,在一切未定之时,近侍左右反倒比监守后方,更容易讨取欢心,明白么?”
曹丕双眼圆睁,不可思议地看着对方,实在不敢相信眼前这个患有疾病,连坐起来都吃力的人就是他追随学习了二十年的荀令君。
荀彧悠悠道:“呵呵,子桓,不要感到意外。我活不了多久啦,自己的身体如何,活到我这个岁数还是能知道个大概的。刚才那些话,是我第一次,也注定是最后一次向你提及。曹公的心意,你需在数年内彻底掌握……”
“令君老师病重了,我去叫医官来!”曹丕心神大乱,全然压不住内心的紧张与恐惧,明知荀令君此刻的话对自己的未来至关重要,却仍不得不打断了他。他唤回了侍从,逃也似的出去了。
荀彧长长出了一缕鼻息,躺正了头,双眼盯着上方,仿佛透过这屋顶,穿过那云层,直看到洪荒去了。
柒
杨修端着酒碗,恣意挥洒着自己的才识与见解,虽然只有曹植一个听者,但他如遇知音般知无不言,比起在丞相与众将面前拆谜解字更加快意。他说了好一阵,终于将话题转入紧要处。
“公子,”杨修道,“之前西征,公子随丞相从军凯旋,新封侯位。此番丞相东讨孙权,留公子在邺,摆明是有监国的意味。自古以来太子君王出征而太子监国,想必丞相心中已经认定公子将是他的继任者了。”
曹植听了,犹豫道:“可是德祖啊,之前我跟父相出征时,二哥也在朝内,这次他也随军去了,跟我的境遇……不是一样的么?”
杨修哈哈大笑,“公子多心了,此一时也,彼一时也!”他一口饮下一碗酒,孩子般手舞足蹈地说,“公子忘记了日前收到的那封急报?董祭酒在许都闹出这么大的事,公子以为丞相会作如何想?”
曹植沉吟道:“父相一向以汉臣自居,现已位极人臣,恐怕不会太在意董祭酒的话吧……何况令君老师也反对了……”
“大错特错!”杨修抢道,丝毫不以曹植为主自己为从而有所收敛,“如果丞相没有暗中授意,借他董昭两个胆子,他也不敢在朝堂之上堂而皇之地大谈晋魏公之事。且荀令君抗辩之后,直到出发劳军都再也没有上朝,公子不会没有察觉到吧?”
“那能代表什么?”曹植疑惑地问。
“公子诗文天赋冠盖古今,偏偏对您父相的心思拿捏不到。”杨修道,“丞相已有晋爵之心,就必会贯彻执行。立国之意明确之后,所做的一切安排,更加了一重含义,公子可知是什么?”
曹植摇摇头。
“给众臣看啊!之前他老人家是丞相,是汉臣,臣位贤者居之,哪有臣子百年儿子接任官位的。现在可不一样,丞相马上就要成为一方诸侯了,诸侯王公的世子,可是要承袭封爵的。”
曹植恍然,站起身道:“德祖的意思是,父相当真有意立我……”
杨修忙做了个噤声的手势,压低了声音说道:“这事,修作为公子属臣为主子谋划,自然可以高声谈论,公子作为主家,却不宜过早表露心迹啊。”
曹植闻言,做了个明白的手势。他深吸一口气,让自己平静下来,柔声道:“德祖啊,你想得未免太多了些,来来来,咱们还是饮酒谈诗!”
杨修笑了,一番功业已在脑海中浮现出来。
捌
荀彧望着眼前空空如也的食盒,久久不能平复内心的波澜。
他早已想到,这一天终究会来,也早已知道,自己将不久于人世。当他尚弄不清是自己先死于疾病还是先死于其他什么原因时,这个无米无肉无菜的食盒摆到了他的面前。
初平二年,荀彧离了寡断少谋的袁绍,投奔刚成为东郡太守的曹操。两人一见如故,长谈三日也不觉疲倦。曹操得意地与人说,“荀彧可是我曹操的张子房啊!”
其后,荀彧不光干着张良的活计,也操持起了萧何的工作。经颍川荀氏人脉为曹操网罗的能人贤士不胜枚举;主理国事内务时,即使曹操遭遇如何惨败,荀彧总能以最优的方式整理残局,转而为曹操谋取更大的利益;任尚书令,则朝中大小事务咸经他手,以汉室衰颓至皇帝几番流离的惨况,他依然匡弼汉主,与曹操一道,将已无人信奉的大汉正统生生延续至今。
一阵剧烈的咳嗽冲破了他回溯的思绪,这一次感觉之剧烈,使他清楚地感觉自己势难见到明天的朝阳。
他仰面摔倒下去,一口浊血喷出,坠在土红色的朝服上,如异兽的怪影将爪牙伸向他的心口。
他艰难地跪坐起来,用尽了全身的力气,伸出右手,想去触碰那个食盒。然而终于触摸不到。随着最后的痉挛由内至外震遍全身,他伸出去的右手颓然落下,与本就垂在身前的左手交在一起,失了一切神采的双眸随着头、颈、背流星般划下,倒在双手之上。
当一早被他严令斥退的侍从在一个时辰后返来,欲伺候他服药就寝时,看到令君荀彧正长长久久地,无比恭敬地,朝那食盒深深叩拜着。
玖
曹操将手中的急报拿得远了一些,方看清简片上的文字。显然,自己已经老了,这双看惯了世间纷乱的眼已然花了。
两个姓刘的果然反目了,刘备斩杀了为刘璋把守益北门户的杨怀、高沛,攻占了涪城。以刘备之能,兼且麾下文武齐备,想来益州这块刘家割据之地,要换另一支宗亲把持了。
他将简片随手扔到案上,站起身来,两侧的侍从忙上来帮他顺直长袍,并将御寒的毛皮捧到面前。他点了点头,待侍从将毛皮披在身上,便走出了帅帐。
北风呼啸着,卷起初解冻的水汽,向着他那红润却也布满皱纹的脸上乱纷纷刺来。他眯起眼,透过茫茫一片,审视着排布齐整的军营,又似纵穿了这片营地,看到了位于远方某处,只有他能看到的东西。
“树木何萧瑟,北风声正悲……”他喃喃念出两句数年前征讨高干时吟作的诗句。彼时乃冬春之交,万物已有复苏之相,只是被凛凛北风逼得不敢抬头。而今又逢冬春时节,大地之上却只有死寂。
那碧眼儿孙权使人在大江西岸驻下重兵,又任那个不下周瑜、鲁肃的吕蒙镇守新修成的濡须口。他的北方将士不畏严寒,但这大江边上湿冷的潮气却让人难受入骨髓去,反倒是南方的兵卒更能适应。
这一仗,还是不好打啊。他在心中暗暗叹息。
他回转身子,走入帅帐,动了下肩膀将毛皮抖落,忙有侍从赶来接住,不曾让毛皮落地。
他的目光聚焦到案上一角,角上静静睡着一个方形物件。那是一个雕工精美的食盒,里面却无米无肉无菜,只满载着沉淀了二十多年的恩情、快意、失落、矛盾,种种情感杂糅,似要把这个食盒膨胀开来。
“文若啊……”
眼窝一松,嘴角苦涩。
而今香何在?
曹操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体会过这种感情,没有尝过这种滋味了。
次年四月,曹操回师邺城。五月,晋爵魏公,邺城更名邺都。
|